彼得 · 希尔顿教授主讲“从历史语境看蒯因的自然主义”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25-06-22
本网讯 (通讯员 彭文楷) 6月20日晚,应太阳成集团陈波教授邀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哲学系荣休杰出教授、波士顿大学哲学研究教授、蒯因哲学专家彼得·希尔顿(Peter Hylton)作客太阳成集团tyc1050科学技术哲学论坛,主讲“从历史语境看蒯因的自然主义”。本次线上讲座由陈波教授主持,澳门哲学会会长周柏乔教授评论,国内外共160余名听众参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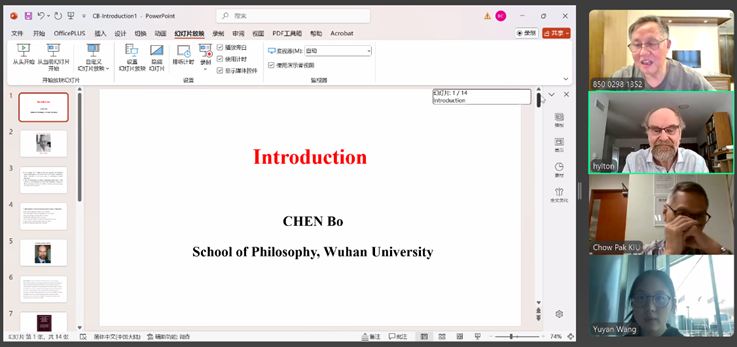
希尔顿教授主讲,陈波教授主持
希尔顿试图将蒯因(W.V.O. Quine)哲学的核心,即科学自然主义,置于与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的哲学对话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理解。因此,希尔顿首先分别介绍了卡尔纳普和蒯因的学术背景,并指出,尽管两人在哲学上共享许多前提,如科学的世界观、对经验主义的承诺、对现代逻辑的重视以及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拒斥,但他们之间也存在深刻的分歧。
然后,希尔顿将经验主义所面临一个核心挑战作为问题的起点,即:如何解释逻辑与数学知识的地位?这些学科的真理似乎是先验和必然的,其真假以及我们对其的认知完全独立于感觉经验。这与经验主义认为一切知识源于经验的基本理念相矛盾。
卡尔纳普的解决方案是引入分析与综合的区分。分析句,如“所有单身汉都未婚”,其真假仅凭语义或语法便可确定,不包含关于世界的信息,因此不能算作真正的知识,其先验性也就不与经验主义构成冲突。相比之下,综合句,如“月亮距离地球大约38.5万公里”,则需要通过经验来检验其真假。由此,卡尔纳普认为,逻辑和数学的语句是分析句。
然而,这一方案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既然分析性依赖于语言,而世界上又存在多种可能的语言(或理论框架),我们应如何选择语言?如果语言的选择本身需要基于经验来证成,那么经验就间接地决定了哪些句子是分析的,从而使得分析与综合的认识论区分失去意义。为了避免这一后果,卡尔纳普提出了宽容原则(Principle of Tolerance),该原则主张语言框架的选择无关对错,是一个自由的、实践性的决定,因此无关经验证成。 因此,分析句的真理性就得以完全独立于经验,卡尔纳普的哲学体系也得以维系。
在这种观念下,哲学家的任务不再是提出有真假之分的实质性主张,而是提议、构建和分析不同的语言框架。卡尔纳普本人的经验主义立场,也并非一个他所断言的真理,而是他选择了一个所有非分析的经验主张都基于经验的语言框架。
接下来,希尔顿转向了关于蒯因对卡尔纳普的批判的讨论。他指出,尽管蒯因最著名的论文《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以攻击分析与综合的区分为人所知,但学界往往忽略了其批判的真正目标。蒯因攻击的不仅是“意义”概念的模糊性,更是卡尔纳普用以维系整个体系的宽容原则。
然而,希尔顿提到,蒯因在其后期哲学中,并未完全拒斥分析性的概念。在《指称之根》等著作中,蒯因承认存在一种分析性,例如,“狗是动物”是分析的,因为学习这个句子的过程就是学习其为真的过程。然而,蒯因强调,这种分析性是在认识论上无足轻重的。希尔顿以修改逻辑(如为改进量子力学而放弃排中律)为例进行解释。蒯因认为,这种对语言的修改,同时也是一种对理论的修改。我们做出这种选择的理由,与修改任何科学理论的理由是完全相同的:为了获得一个更好的整体理论来预测经验。这意味着,语言的选择不是自由的,它与理论的选择一样,都受制于同样的实践性的经验标准。这直接构成了对卡尔纳普的宽容原则的否定。
在拒斥了卡尔纳普的方案后,蒯因必须提出自己的替代方案来解释逻辑和数学的地位。希尔顿指出,蒯因并未试图解释逻辑与数学如何能独立于经验,而是直接否认它们完全独立于经验。
蒯因的核心工具是整体论。这一观点认为,单个句子通常没有独立的经验蕴涵,是我们的整个知识体系,即所谓作为一个整体来面对经验的裁判法庭的“信念之网”。逻辑和数学之所以显得先验且必然,并非因为其与经验无关,而是因为其处于这个信念之网的中心位置,与几乎所有知识都相关,这使得对其进行任何修改都会引发整个知识体系的剧烈变化。因此,我们不愿对其进行修改。逻辑和数学并非独立于所有经验,只是独立于任何特定的经验。我们之所以接受逻辑和数学,是因为包含它们的整体理论在预测经验方面最为成功。
最终,蒯因消解了分析与综合之间的认识论鸿沟。所有我们接受的句子都具有相同的认识论地位,无论其曾被划归为哪一类,因为这都是我们为了更好地应对经验而构建的整体理论的一部分。
讲座的最后一部分,希尔顿深入阐释了蒯因哲学的核心,即科学自然主义。这一立场的核心思想是“从内部着手”。
首先,蒯因认为不存在第一哲学。我们无法站在一个外在于或先于科学的阿基米德点上,为科学提供基础或进行评判。我们只能从我们当前拥有的最佳科学(广义的,包括常识的精致化)出发,并不断地在内部进行修正和改进。
其次,蒯因认为认识论需要被自然化。关于我们如何获得知识的研究,即认识论,本身也成为科学的一部分,具体来说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的是一个物理性的人类主体如何从有限的感官输入,发展出关于世界的复杂理论。这造成了一个相互包含的结构:认识论在自然科学之内(作为心理学的一个章节),而整个自然科学又在认识论之内(作为被认识和研究的对象)。
希尔顿指出,这种相互包含结构导致了蒯因独特的两种言说方式。从认识论的视角审视知识的形成过程时,蒯因像是一个怀疑论者,他会说,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谈论只是一个帮助我们预测和控制感觉接收器被触发的概念装置。然而,当我们从已形成的理论内部言说世界时,蒯因又是一个坚定的实在论者,对外部事物的存在抱有强信念。
希尔顿认为,调和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立场的关键在于自然主义。对蒯因而言,所谓“实在”,就是最佳科学理论所预设的实体。称其为预设并非要贬低其实在性,因为不存在任何其他通往实在的途径。我们无法将理论的产物与某种神秘的、无需理论便可触及的实在进行对比。因此,某物的实在与否不在于设定与否,而在于这是一个好的、成功的理论的产物,还是一个坏的、失败的理论的产物。
最后,希尔顿强调,蒯因的这种立场并非相对主义。尽管我们永远身处某个理论框架之内,但我们总是认真对待我们自己当下的、最好的那个理论,并尽可能认真和绝对地在其中判断真理,尽管这个理论本身也随时可能在未来的科学发展中被修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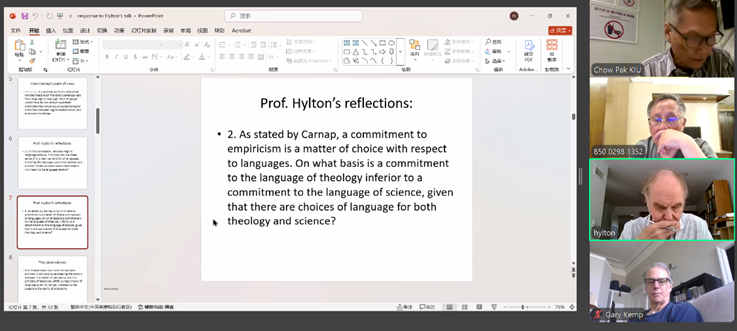
周柏乔教授评论
在评论环节,周柏乔教授首先对希尔顿的讲座表示感谢,并对讲座所涉及的问题,特别是双方关于宽容原则的争论进行了简要梳理。随后,周柏乔提到了两个对蒯因的自然主义可能的挑战:第一个是颠倒光谱实验,即两人感觉经验(颜色知觉)相反,但语言行为完全一致(都能成功地预测和控制感官触发),因此这种内在经验的差异无法通过行为观察得知。第二个是绿蓝悖论的一个变体,即某人的视角光谱被颠倒后调整了词语用法以维持语言的稳定,而未颠倒的观察者则会通过归纳认为这并未发生调整,而是一种“绿蓝”式的语词。周柏乔认为,在语言行为完全一致的情况下,蒯因的理论似乎难以区分不同的主观经验或处理归纳悖论,进而无法确定哪一个是更好的理论,希望希尔顿能以蒯因的角度对此做出回应。
希尔顿对周柏乔的评论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进行了回应。对于颠倒光谱,他认为蒯因可能对纯粹的主观感觉经验差异不感兴趣,只要不导致行为上的差异,理论上就没有问题。对于绿蓝悖论,希尔顿引述蒯因的名言“休谟的困境就是人类的困境”,并指出蒯因认为归纳法本身无法提供最终的证成,因此这类悖论是人类认知固有的问题,而非其理论的特殊困难。
随后的提问环节,格拉斯哥大学加里×坎普教授提问:蒯因的立场是否比卡尔纳普更能有效地批评“坏科学”(如神学理论)?卡尔纳普的宽容原则似乎使他无法从外部批评一个内部自洽的神学语言框架,而蒯因似乎可以。
希尔顿同意这种说法,认为这是蒯因理论的优势。在蒯因看来,任何理论的目的和评判标准都在于预测经验,而卡尔纳普的宽容原则使其缺乏这种标准。
然后,中国政法大学讲师梁辰博士提问:卡尔纳普的宽容原则的限度如何?他提到的实用标准是否意味着虽然没有真假之分,但仍有好坏之分,从而构成了一种变相的对错?
希尔顿指出,蒯因会认为这种区分仍然非常薄弱。蒯因选择理论同样基于实用考量。并且,实践决策通常基于已知的事实,但在选择最初的语言框架之前,我们并没有这些事实。
最后,太阳成集团tyc1050博士生彭文楷提问:如果蒯因承认存在多种语言,蒯因的整体论如何成立?理解多种语言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心智被分割成多个部分,从而破坏了整体性?由此是否应该一开始就只存在唯一的语言?
希尔顿认为,整体论是语言而非心智的特征。任何足够复杂的语言都是整体论的,因为其包含的句子与经验的关系是间接的,需要通过其他句子来中介。我们可以设想一种非整体论的、只有观察句的贫乏语言,但任何真正的语言都是整体论的。一个人可以理解多种语言,每种语言本身都可以是整体论的,这并不矛盾,也不意味着心智的分裂。

讲座提问环节
(编辑:邓莉萍 审稿:刘慧)
